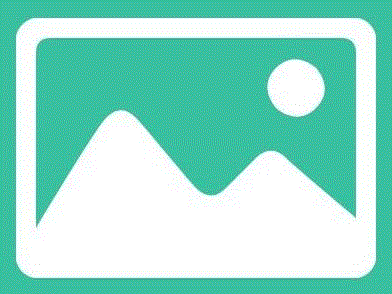吴思敬简介
吴思敬: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诗探索》主编。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。享受国务院颁发的“政府特殊津贴”,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主要学术著作有:《诗歌基本原理》、《诗歌鉴赏心理》、《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》、《冲撞中的精灵》、《心理诗学》、《诗学沉思录》、《走向哲学的诗》、《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》、《吴思敬论新诗》、《中国当代诗人论》、《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》、《文学原理》(主编)、《中国新诗总系·理论卷》(主编)、《中国诗歌通史》(与赵敏俐共同主编)、《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》(主编)等。
吴思敬: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《诗探索》主编。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。享受国务院颁发的“政府特殊津贴”,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主要学术著作有:《诗歌基本原理》、《诗歌鉴赏心理》、《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》、《冲撞中的精灵》、《心理诗学》、《诗学沉思录》、《走向哲学的诗》、《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》、《吴思敬论新诗》、《中国当代诗人论》、《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》、《文学原理》(主编)、《中国新诗总系·理论卷》(主编)、《中国诗歌通史》(与赵敏俐共同主编)、《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》(主编)等。
鸟啼花落,皆与神通
吴思敬
袁枚《续诗品》中有一首《神悟》,其中有句云:“鸟啼花落,皆与神通,人不能悟,付之飘风”。袁枚认为,“神悟”这种本领不是一般人都具备的,能有这种悟性的只能是诗人。无独有偶,袁枚的看法在一些西方诗人和艺术家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。俄罗斯诗人巴拉廷斯基曾这样描写歌德:“他和大自然呼吸同一的生命,/懂得小溪的潺潺,/听出树叶的低语,/感觉小草的滋生;/他精通星辰的书,/大海波涛和他密谈。”(巴拉廷斯基:《吊歌德之死》)。别林斯基在论述莱蒙托夫诗歌的时候,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:诗人,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,他就比别人更透彻地懂得自己和宇宙万物的亲密关系以及血肉联系;当他是一个青年的时候,他就已经把它们的无声的言辞,它们的隐秘的私语,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语言……他是一种富有感受的、易受刺激的、永远积极活跃的有机体,只要和外界稍微接触一下,就会迸发出电火花来”(《别林斯基选集》第二卷)。法国画家霍安•米罗则这样谈自己的亲身体验:“当我观察一棵树时,一棵在我家乡卡塔洛尼亚很有代表性的树,我就感觉到它在跟我谈心,它似乎也有眼睛,人们能同它谈话。一棵树能通人情,连一颗小鹅卵石也是如此”(《霍安•米罗访问记》)。
袁枚所标举的“神悟”,以及在西方大诗人、大艺术家身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现象,是诗人所独具的一种心灵禀赋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过:“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严羽所说的“别材”、“别趣”,其实主要也就是指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悟性。
这种悟性从哪里来?从根本上说来,要求诗人是个冰洁玉清,内心怀着炽烈的爱的“处子”,要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童心。真正的诗人都是“自然”的儿子,他总是怀着对自然的深情,用人的眼光、人的感情来看待自然。他胸中充溢着一股爱的暖流,就像生命源泉中流出的小溪,在潺潺流动,一遇到阻隔或被风吹动,便会泛起层层涟漪。从心理学上说,在主观与客观最美妙契合的刹那,在潜意识中酝酿已久的思维成果就会一下子涌现到意识世界中来,如同电光石火般照亮人们的思路,闪现出一些奇思妙想,这就是所谓“神悟”了,透过这种神悟,诗人就能够见微而知著,能从“梅花开时雪正狂”想到山花烂漫的春天,能从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觉出即将到来的狂飚,能从一般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美,发现诗。
然而这些年来,在中外大诗人中屡见不鲜的“神悟”现象,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诗歌叙事性写作浪潮中,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、被遮蔽了。一些诗人把诗歌写作等同于生活现象的实录,还有人标榜自己的写作的诗歌是“日记体”,于是生活中的一些七七八八的琐事也就唐而皇之地写进诗中,枯燥乏味,无聊,无趣,倒了读者的胃口。须知日记是日记,诗是诗。日记是天天可写的,诗的灵感却不是天天都能降临的。在诗情袭来的时候,可能在日记中写出一首诗;但寻常的日记内容,即使分行写下来,也不可能是诗。为什么?就是由于在这类作品中缺的是诗人对诸种生活现象的悟。
还有些诗人是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有个有名的说法:“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”,在他看来,“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,也不是荒诞的。它存在着,如此而已”(《未来小说的道路》)。阿兰•罗布-格里耶强调物是客观存在,物就是物,不存在什么物我一致,物我同心。要求作家从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事物做客观的记述,而不作任何解释。至于作家写了什么,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好了。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的小说,被称作“客体小说”。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观点传入中国后,受到部分先锋派诗人的激赏。阿吾等推出的客观呈现生存环境的“不变形诗”《对一个物体的描述》,杨黎的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等便是受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影响写出来的。现在看来,这些作品除去在先锋诗歌史上留下了实验性写作的痕迹外,作为诗歌创作的模本,已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了。
最后,再说两句。凡人做诗,一题到手,必有一些供给、应付的套语,如老僧常谈,不召自来;也必有一些寻常的意象、琐碎的事物,奔涌到笔下。若诗人必如谢绝泛交,尽行麾去,心精独运,自出心裁,才能写出佳作。诗人不写则已,要写就要让作品有独自的神思,独自的面貌,独自的风采,所谓“不践前人旧行迹,独惊斯世擅风流”。而要做到这点,需要诗人多方面的准备,其中尤为不可忽视的,便是面对“鸟啼花落”等日常景象而引发的神悟。
袁枚所标举的“神悟”,以及在西方大诗人、大艺术家身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现象,是诗人所独具的一种心灵禀赋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过:“诗有别材,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,非关理也。”严羽所说的“别材”、“别趣”,其实主要也就是指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悟性。
这种悟性从哪里来?从根本上说来,要求诗人是个冰洁玉清,内心怀着炽烈的爱的“处子”,要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童心。真正的诗人都是“自然”的儿子,他总是怀着对自然的深情,用人的眼光、人的感情来看待自然。他胸中充溢着一股爱的暖流,就像生命源泉中流出的小溪,在潺潺流动,一遇到阻隔或被风吹动,便会泛起层层涟漪。从心理学上说,在主观与客观最美妙契合的刹那,在潜意识中酝酿已久的思维成果就会一下子涌现到意识世界中来,如同电光石火般照亮人们的思路,闪现出一些奇思妙想,这就是所谓“神悟”了,透过这种神悟,诗人就能够见微而知著,能从“梅花开时雪正狂”想到山花烂漫的春天,能从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觉出即将到来的狂飚,能从一般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美,发现诗。
然而这些年来,在中外大诗人中屡见不鲜的“神悟”现象,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诗歌叙事性写作浪潮中,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、被遮蔽了。一些诗人把诗歌写作等同于生活现象的实录,还有人标榜自己的写作的诗歌是“日记体”,于是生活中的一些七七八八的琐事也就唐而皇之地写进诗中,枯燥乏味,无聊,无趣,倒了读者的胃口。须知日记是日记,诗是诗。日记是天天可写的,诗的灵感却不是天天都能降临的。在诗情袭来的时候,可能在日记中写出一首诗;但寻常的日记内容,即使分行写下来,也不可能是诗。为什么?就是由于在这类作品中缺的是诗人对诸种生活现象的悟。
还有些诗人是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有个有名的说法:“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”,在他看来,“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,也不是荒诞的。它存在着,如此而已”(《未来小说的道路》)。阿兰•罗布-格里耶强调物是客观存在,物就是物,不存在什么物我一致,物我同心。要求作家从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事物做客观的记述,而不作任何解释。至于作家写了什么,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好了。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的小说,被称作“客体小说”。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观点传入中国后,受到部分先锋派诗人的激赏。阿吾等推出的客观呈现生存环境的“不变形诗”《对一个物体的描述》,杨黎的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等便是受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影响写出来的。现在看来,这些作品除去在先锋诗歌史上留下了实验性写作的痕迹外,作为诗歌创作的模本,已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了。
最后,再说两句。凡人做诗,一题到手,必有一些供给、应付的套语,如老僧常谈,不召自来;也必有一些寻常的意象、琐碎的事物,奔涌到笔下。若诗人必如谢绝泛交,尽行麾去,心精独运,自出心裁,才能写出佳作。诗人不写则已,要写就要让作品有独自的神思,独自的面貌,独自的风采,所谓“不践前人旧行迹,独惊斯世擅风流”。而要做到这点,需要诗人多方面的准备,其中尤为不可忽视的,便是面对“鸟啼花落”等日常景象而引发的神悟。
2025年7月10日
(原载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7月24日)
(原载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7月24日)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序言
吴思敬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的两位对话者,都是我十分热爱的学者和诗人。他们著作等身,杜书瀛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,邵燕祥先生是著名诗人、杂文家。他们的对话自然会随时爆起灵感的火花,引领读者进入一片思维的新天地。邵燕祥由于身体原因,后来不能再一一作书答复,但杜书瀛此后的论诗书也并非单纯的心灵独白,他依然是有明确的对话者存在的,这是基于杜书瀛与邵燕祥几十年的友谊,基于杜书瀛对邵燕祥人格、思想以及诗学观念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。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的新诗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,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,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与借鉴,不断推出的“新理论”、“新观念”、“新方法”,再加上所面临的不断变换的诗歌新格局与生态环境,使这些年的新诗理论与创作界呈现了一种蓬勃发展,但又众说纷纭、矛盾抵牾的混乱局面。因此,目前亟需用科学观念来对新诗理论与创作的现状予以反思、清理,以促进新诗理论与创作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。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。这是一部谈诗的书,围绕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当下诗坛状态而展开,作者试图改变以往理论文字那种面孔冷峻、不苟言笑的呆板文风,故采用了书信体,两位对话者均以活泼的语言,娓娓而谈,由此既可以见出两位老友之间几十年的感情,又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对诗歌的热爱,以及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。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,不是就事论事,而是针对诗歌理论与创作的中的问题,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。作者的创新性思维涉及到关于诗歌的基本特征、关于诗歌发展方向,关于百年新诗史、关于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等方面,作者既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,同时也对当下诗坛存在的“晦涩”、“读不懂”、“贵族化”、“神秘化”、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诗”、“知识分子写作”、“民间写作”、“下半身写作”、“打工诗歌”、“底层写作”、“机器人写诗”等敏感而富有争议的问题,表示了自己的看法,这有助于廓清诗歌理论界与创作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与片面观点,对新时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。
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鲜明的思辨性与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交织。作为著名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,杜书瀛熟悉中外美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主要理论与流派,善于从理论高度,对当下诗歌理论使用的“诗歌”“象征”“隐喻”“韵律”“节奏”“象征派”“格律派”“朦胧派”等概念做了认真的疏理与辨析,并对相关术语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,显示了出色的思辨能力,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认知。不过,杜书瀛的另一重身份,即诗人身份,在这本《宅居谈诗》出版前了解的人恐怕还不多。其实,在诸种文学形式中,杜书瀛最爱的是诗。他说:“我一生虽然不主要研究诗,但我一直关心诗,热爱诗,也读了不少诗,直到今日耄耋之年仍然乐此不疲。(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)。杜书瀛不止爱诗、读诗,而且还写诗。他把诗歌看成是抒发内心情感,排解胸中块垒,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,写诗不求发表,有的藏之箧底,有的则在书信、邮件中与朋友互相交流。我曾有机会读到过他自称“打油”的诗作,实际是非常认真的书写,无论直抒胸臆也好,借物喻人也好,写所见所闻也好,全发自内心,亲切感人,而非游戏笔墨。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“真”,抒真情,说真话。他的《我只是一个老鸡公》不只是自白、自嘲,更把自己的主观情思附丽在“老鸡公”这个意象上:“当黑夜/即将逝去/我仍会按时报告天明/但我/无资格以此居功/也不值得别人称颂”。他另有题为《三条小溪——赠三个女孩》的一首诗,来自于一次会议中与三个女孩的接触,写得清新活泼,用小溪的意象暗示女孩:溪水的清澈暗示她们的纯洁,溪水的流动暗示她们的活泼,溪水的歌唱暗示她们的情怀。全诗就像溪水一样灵动、透明、清亮,这三个女孩就在她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刻被定格了,成为诗美的结晶。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,使他的艺术感觉分外敏锐,诗的悟性更强,所以在他品评诗人诗作的时候,会“眼逢佳句分外明”,写起文章来会笔锋常带感情,议论切中肯綮。
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诗歌评论文体的创新。杜书瀛曾写过一本书《从“诗文评”到“文艺学”》,这是从理论角度对古代“诗文评”到现代“文艺学”进行的系统探索与研究。作者认为,体系总是试图给人一套规范式的东西,这套东西经常管制着人家,成为所谓知识-权力结构。而中国的“诗文评”,很少有类似西方的“体系”,中国诗学更多的是点评,其特点是要言不烦,一语中的,直击要害,点到为止。《宅居谈诗》则是他继承古代“诗文评”的传统,改变文风的一次实验。《宅居谈诗》没有宏大的结构,没有复杂的层次,就是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写下来, 每封信大致谈一个主题,一封信谈不透,下一封信可以接着再谈。他明白“话需通俗方传远,语必关风始动人”,他要的就是那种活泼泼的,为读者喜闻乐见的“亲民”文字。这种继承古代“诗文评”传统的写作趋势,到近期所写的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和《读王单单〈花鹿坪手记〉手记》就更明显了。以《读路也》的写作过程为例,我先是在邮件中分期分批地向杜书瀛转发了路也的诗,他边读边写下札记,然后我把杜书瀛的意见转告路也,再把路也的意见反馈给他。后来我则把路也的联系方式给了他,让他与路也直接对话。实际上,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这篇精彩的诗歌评论,正是运用“诗文评”的方式解读当代诗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。
比起一般读者,我是比较早的就读到了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的最初文本的。越读越爱读,不仅作者所讲的诗学理论、所做的诗人评论深得我心,而且我也深深感到杜书瀛以耄耋之年写出此书,他不只是谈诗,其实也是在谈怎样做人。“诗乃人之行略,人高则诗亦高,人俗则诗亦俗,一字不可掩饰,见其诗如见其人”(徐增:《而庵诗话》)。最近几年,我们经常互通邮件和电话,使我更透彻地了解了他的内心和为人。2021年9月24日,他给我转来巴金的一篇文章,并附了一段他的感想,他说巴金“说的是觉悟之言,是真心话。对我们、特别是对我,是非常有用的话,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。而且我也与巴金有同样的感觉。只是我同他在文革十年觉悟的过程是不大一样的。十年文革,我第一年造反,是彻底的‘奴在心者’(以‘奴在心者’的心,走错误的路);等到后面的九年挨整乃至自杀未遂时,我才渐渐觉悟了,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,我的‘心’觉醒了。当‘心’觉醒之后,倘若今天有人企图让我回到‘奴在心者’的状态时,我是绝不干的——也不可能回去了。回不去了。我的那篇《说自己的话》(发表在《随笔》),就是我走出‘奴在心者’之后的写照。也许我还不够彻底,但我基本上是‘自己’了。对谁,对什么事情,我在没有弄清楚之前,再也不盲目跟从了,再也不迷信了”。杜书瀛是至诚君子,他说到做到。就以《宅居谈诗》的写作而言,他评论了从新诗草创时期的胡适,到当下最活跃的青年诗人,也涉及了许多敏感而有争议的热门话题,他所持的原则是说自己的话,既不想去讨好谁,也不想去为难谁,不遮遮掩掩,不吱吱唔唔,有好说好,有坏说坏,不做违心之言。读他的文章,你会感到很自然很痛快,支持什么,反对什么,一目了然;而不像当下的某些诗评,用一连串的引文,外加密密麻麻的注解,疙里疙瘩,貌似高深,却是云山雾罩,不知所云。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态度。作者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探索,又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之处,既不去“捧杀”,更不去“棒杀”,而是表达了一位前辈作家对后代诗人的温暖关怀与殷殷期望。
我曾在《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——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》的序言中,引用过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讲的“金蔷薇”的故事,称“邵燕祥就像这位巴黎清洁工,但他收集的不光是尘土,还有他的苦难,他的血泪。他把这一切凝结在一起,打造成了诗的金蔷薇,献给他终生热爱、不离不弃的祖国和人民。” 杜书瀛是邵燕祥的知音,在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中对邵燕祥的诗歌和为人做出了崇高评价,并视他为“排在第一位的我最尊重的朋友”。在我看来,杜书瀛本人以他博大的爱心、独立的人格、卓越的学识同样赢得了朋友们的友谊与敬重。为此,我把凝聚着杜书瀛心血的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》书》也看成是他献给祖国、献给新时代诗人的珍贵礼物——一朵金蔷薇。
2022年10月22日
(原载杜书瀛著: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菩祥书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,
另刊于《文艺争鸣》2023年第7期)
(原载杜书瀛著: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菩祥书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,
另刊于《文艺争鸣》2023年第7期)
责编:安娟英